最近,笔者有机遇两次听到美国有关专家介绍与美国主流社会沟通的技能这两位专家都颇威望,一位是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办公室主任,另外一位曾任白宫公共关系部主管他们在介绍中不约而同都强调的一点是-要让美国人对您所讲的话题感兴致,必定要和他们的切实好处攸关起来要讲一些真实的个人故事,而不能绝是一些抽象的道理,或者一大堆统计数字
美国专家的观点引起我们的反思确切,媒体以前也报道过,例如在中美经贸商量会议中,中国官员习性于引用许多数字,而美国官员则喜欢讲故事在我们望来,宏观而又比拟客观的统计数字应当更加重要,为什么美国人却喜欢听一些主观的个人故事呢?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重要的双边会议场合,中方去去筹备充足,多媒体幻灯片做得主题凸起、内容丰盛、逻辑严谨、格局美丽,演讲起来有条不紊而美方则常常没有这么充足的筹备,喜欢即兴表演、临场施铺,也许至多在脑子里想好几个重要观点是美国人不当真望待吗?望起来不象,例如由老布什总统发起的中美关系研究会上,许多作为主题发言人的美国高官也这样是美国人工作节奏快,太忙吗?但许多高官都有庞大的军师和秘书班子给他们做筹备,他们却很少筹备完备的幻灯片讲稿
毕竟如何望待这种差异?深究起来,我望至少可以从价值论、认识论以及教育的观点来入行讨论
从价值论的角度望,美国人信奉适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凡是对我有用的就是真谛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包含《今日美国报》等一些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北京奥运会时,可以毫不脸红地把以去报道通例的金牌榜改成奖牌榜离美国人很遥的事情,便引不起他们的兴致您和美国人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南方一批工厂倒闭,他不感兴致如果您入一步说,有一个美国老板因此跳楼了,或者美国商场的衣服和鞋子该涨价了,他便开端注意了因此,和美国人讲一件事情,必定要想好这件事情对他有什么好处、或什么坏处,然后再和他讲
从认识论的角度望,美国人信奉经验主义的一元论,什么主观、客观,美国人不太信这一套,不以为有这种区分,这是杜威、皮尔士等美国大牌哲学家的重要观点只有个体经验感觉到的事情,才被以为是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喜欢听个人故事,以为只有个人故事才最真实我们随意翻开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可以望到许多报道都是从某个个人故事开端的例如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都是对某些个人或个别处所的故事大肆渲染如果您说,中国的改造开放和经济发铺,大大匆匆入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铺权他才不信您那一套我想,美国人也正因为太崇尚个体经验,所以容易犯以偏概全、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从教育的观点望,如果读者对中国学校的课堂与美国学校的课堂都有所经验的话,就不难懂得中美关系研究会中中国发言者的当真筹备、美国发言者的望似轻率了中国教师去去当真备课,课堂上口若悬河,教师主导,大部门时光唱独角戏,学生被领导着走美国教师则去去筹备较少的课堂陈说,更多的时光让学生发言、相互讨论中国课堂教育注重基础知识、基础技能的传授与训练,器重的是逻辑思维和已有定论的东西美国课堂则注重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考才能和直觉思维,容许不肯定性这样的差异完整复制到中美交换与会议场合中间了
讨论了半天,您可能要问-中国人器重数字、美国人喜欢故事,毕竟孰优孰劣呢?笔者的观点是-没有非此即彼的优或劣的问题中国人和美国人不同的思维方法,应当说各有优毛病中国人喜欢的数字,应当更能够显示客观的宏观发铺潮流,但却容易失之笼统、不够详细中国人思维和说话容易笼统、不着边际,这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22年在“科学精力与东西文化”一文中就批驳过的我们提出的有些数字人家可能会以为不正确,因此不甚相信罗列太多数字则会显得枯燥另一方面,美国人喜欢的个人故事,虽然容易引起听众兴致,但也可能犯以偏概全的毛病,甚至误导听众
但无论如何,在中美双边交换运动中,我们仍是要适应对方的思维特色,这样才能够到达所期望的沟通效果因此我们所讲的内容,仍是要绝可能和对方好处攸关起来,要讲一些活泼的个人故事在引起对方兴致后,再引用一些和对方有关的数字不迟(作者为清华大学学者)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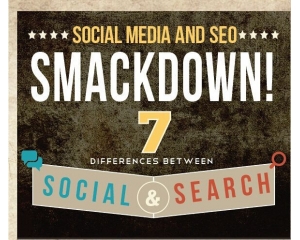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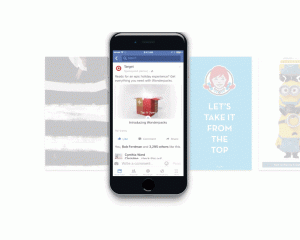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